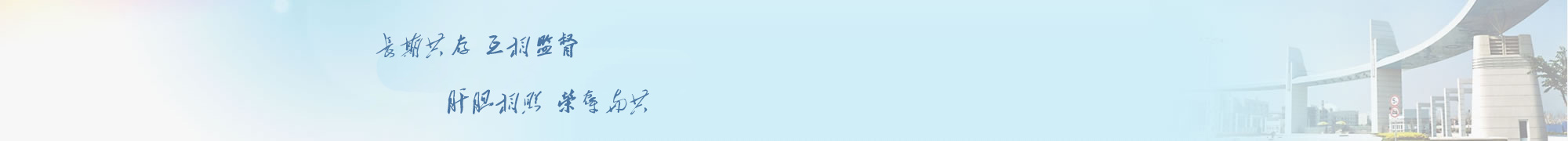为了誓言
作者:昌社育
为 了 誓 言
——记 萍乡民革老同志贺殷威
遵守党的章程
听从党的指挥
服从党的纪律
决不反悔
……
这是贺老1949年4月3日加入民革时的誓言,54年过去了,现已八十一岁的贺老仍没忘记曾经的誓言。
被萍乡民革全体党员尊称为“贺老”的贺殷威,是地下时期加入民革的老同志,曾任民革萍乡支部主委、民革市委一、二、三届顾问、萍乡黄埔同学会会长,他亲历了江西民革50多年的发展历程。几十年来,贺老为民革的事业殚精竭智,为萍乡民革的发展壮大奉献了自己。在纪念民革江西省委成立50周年之际,我专程采访了贺老,他用朴实的语言为我讲述了过去那难忘的一幕一幕,而对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一切,只说了句:“都是为了誓言!”
一、投笔从戎、立下誓言
1922年,贺老出生在今天的安源区青山镇葡萄村,虽然父亲曾任安徽高级法院的庭长、四川高等法院院长,但幼年的他并未得到父爱,只是在亲友的资助下,才勉强读完了高中。1939年,抗日热潮风起云涌,凭着一股男儿热血,17岁的他投笔从戎,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抗战时期,军校的生活的非常艰苦,但艰苦的环境锻炼了他坚强的性格。训练中,不管是投弹、射击,还是攻防对抗训练、兵器拆卸,他样样领先。大雪的夜晚,学校进行夜间训练,要求每位学生全副武装,在雪地里行军100里,贺老他们只能穿着单薄的军装,行进在雪地里,脚肿了,嘴唇紫了,他咬着牙走了过来,结果学生中年纪最轻、个子最小的他却名列第一。由于他训练刻苦且敢于直言,战友们送他一个外号——“小钢炮”。
1941年7月,贺老从军校毕业了,被分配到江西省军管区司令部,由于是战时,工作地点都比较分散,贺老也到处奔波,他曾在丰城县国民兵团常备二中队任少尉队长、宁都国民兵团任少尉督练员,也在司令部兵役宣查队任中尉队员、征募处档案室任上尉书记官、第三科上尉科员,直至抗战胜利后,军管区司令部才回迁南昌,贺老任第二科上尉参谋。
虽说抗战胜利了,可当时的局势还非常动荡,物价飞涨、官场腐败、民不僚生,对此,贺老也是满腹的疑惑,但无人诉说,直至遇到了他的领路人黄鸣九。黄鸣九当时是省军管区司令部的中校主任参谋,既是贺老的上级,也是他的同学,在闲谈中,黄鸣九问起对时局的看法,贺老“小钢炮”的性子又发了,一口气把满腹的怨气一股脑地倒了出来。黄鸣九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走新的路,只有这样国家、百姓才有前途,我们要走孙中山先生指引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路,新路有新书,我借给你看吧。”于是贺老陆续读到了《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
1949年4月3日,当时已是民革江西省筹委会委员的黄鸣九,又来到贺老住处,他说:“根据民革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时发表的宣言和制订的《行动纲领》,民革以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为目标,你愿意加入吗?”这是贺老第一次听说“民革”二字,但他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右手宣誓:“遵守党的章程,听从党的指挥,服从党的纪律,决不反悔……”。他说:“我就认准孙中山,要做他的真实信徒。”也就从这一刻开始,他就立志把自己献给了民革。宣誓后,黄鸣九传达了民革江西省分部代主委廖超伦的指示:派贺老和另外两位同志回萍乡发展民革地下组织,开展反蒋民主活动。那份入党誓词,贺老小心地把它折成一小块,藏在火柴盒底,带回了萍乡。
二、坚定信念、走向光明
当时萍乡城内,人心混乱,谣言峰起,人民解放军日益逼近,国民党军队和萍乡县城官僚纷纷弃城逃跑。贺老认为,这正是宣传的大好时机,于是,他白天在家里写好标语,磨好浆糊,用竹筒装好,晚上,利用夜幕的掩护,他和民革的同志在青山到萍乡城的路旁树上、电线杆上,在城里的街头巷尾,张贴“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等反蒋拥共的标语。回忆往事贺老说:“在漆黑的夜晚,一个人在十几里的路上贴标语,说不怕还是假的,一是怕遇到熟人,二是怕国民党特务,但在第二天看到国民党官僚惊慌失措的神情,听到老百姓风传‘解放军昨天晚上进城了’,心里的害怕也就变成了欣慰了。”
湘东浮桥是当时湘东境内萍水河上唯一的通道,当时国民党五十八军有一个连把守,为阻止解放军南下,他们在桥上铺满柴草,放置煤油,准备在撤退时烧毁浮桥。得知这一消息贺老连夜发动民革同志,并联络当地父老乡亲,凑足了100块银元,送到该连连长手上,买通连长,希望他不要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通过贺老他们的工作,该连长放弃了烧桥的念头,弃桥而逃,从而保住了浮桥,也保证了解放军顺利南下。为维持社会秩序,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保持人心稳定,贺老还组织乡亲在晚上守护铁路;在解放军过境时,又和乡亲们一起夹道欢迎,为解放军送茶送水。
在开展活动的同时,还积极发展民革组织,很快民革地下组织就发展到30余人,其中既有国民党政权机构中的进步人士,也有煤矿、钢厂的高级职员。针对国民党制造的“共产党共产共妻”等谣言,民革成员配合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宣传共产党在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驳斥各种谣言。在解放军进城后,又积极协助新政府收购粮食,加工军粮。1950年春节,贺老还专门组织了一支秧歌队,走村串户,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
1950年4月,民革江西省分会派蒋今清、黄鸣九两同志来萍进行组织整顿,经整顿,保留了16位同志,同时宣布成立民革萍乡县工作小组,贺老当时任副组长。小组成立后,萍乡的第一任县长盛朴专门召见民革同志,并说:“请友党同志支持政府的工作,同时,希望大家加强学习,多了解政策,积极开展活动配合中共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可向我反映。”经中共组织批准,安排贺老担任了小学教师、校长,从此他就没有离开过教育战线。“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信任,也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贺老感慨地说。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贺老和民革的同志们结合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各项中心工作进行学习和宣传活动,如:参加土地改革、大炼钢铁、反右等,直至1966年文革开始,民革支部停止了活动。文革期间,贺老因严重的“海外关系”,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批斗,家也被抄得一无所有,直到1971年才得到“解放”,重新回到教学岗位。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坚信,自己的信念没有错。
三、殚精竭智、壮大民革
在萍乡民革广大党员中有一个说法:“贺老一只包拎起了萍乡民革” , 这话还有个由来。
1979年,民革省委秘书长黄鸣九来萍乡,恢复民革组织,贺老担任主委,但经过十几年的风雨动荡,民革党员仅剩七名同志,为此,发展党员成了贺老工作的重点。头戴深蓝色的尼绒鸭舌帽,身穿青布中山装,手里提着一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脚上穿一双褪了色的解放鞋,这是贺老当时的“标准装束”。而这只黑提包里就装着支部的公章、民革党程、入党申请表及学习资料,贺老把它戏称为“提包办公室”。提着这个包,贺老四处奔走,发展党员。为发展在湘东镇阳干中学任教的一位年轻教师,贺老从萍乡乘车到湘东,再要走上十余里路,找到这位同志,向他讲解了民革的章程和历史,面对这位同志疑惑的神情,贺老由远而近、由浅而深,作细致的开导工作,他说:“民革不是以前的国民党,而是一个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组织,作为一个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年,加入民革一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二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方方面面的知识;三可以促进你在政治上的进步、事业上的发展,年轻人只要努力干,就会有出息的。”此后,贺老又三次到他单位,送去学习资料,与他谈心,贺老的诚心打消了这位同志的疑虑,光荣地加入了民革组织。凭着热情和真诚,在贺老及民革支部全体同志的努力下,到1982年11月,民革党员由7人发展至29人,民革萍乡市委成立了筹备委员会,贺老为召集人之一。
筹委会首先面临办公用房、经费、专干编制三大困难,此时,贺老已是六十岁的老人,可他为了民革的事业,又拎着那只黑提包,四处奔走。 为借调当时在效区中学和三田煤矿的黎恩荣、宋华铿两同志(黎恩荣曾任市人大副主任、民革市委副主委,现任市政协副主席,宋华铿曾任民革市委副主委,现为市政府参事),他曾四次到三田煤矿,三次到效区中学与中共组织商谈,把他们调入机关工作。1985年元月,市委会正式成立,考虑自己已退休,年龄也大,贺老只肯担任顾问之职。在民革市委会成立的时候,贺老还是提着那只黑提包,同志们都笑称贺老是用一只包拎起了萍乡民革。
四、古稀之年、情系教育
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每年的这天支部都开展纪念活动。1982年的11月12日的纪念活动与以往不同,在这次支部会议上,作出了一项对萍乡民革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决定,那就是发挥民革党员的自身优势,兴办学校,以此作为萍乡民革走向社会的切入点,希望通过办学的方式,宣传和发展民革组织,扩大民革在社会上的影响。经大家商议,将学校命名为——萍乡市中山业余学校(后改名为萍乡市中山学校)。
1983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五十八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萍乡市中山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市教委、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出席了开学典礼,中山学校正式成立了。此时,贺老已退休,按理是该享清福的时候了,但为了民革的事业,也是为了自己魂牵梦系的教育事业,他毅然挑起了中山学校校长的重担。
贺老的家在离市区八公里的西郊,中山学校开办初期,他每天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步行两公里到路边挤公共汽车,学校经费不足,他就自己掏钱买票。当时,正值他老伴重病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贺老在奔波了一天回家后,还要照顾自己的老伴。贺老面临两难的选择,一边是相依相伴数十载的妻子,一边是自己为之追求、为之奋斗的民革事业。儿女们都劝他,不要这样辛苦,留在家里多陪陪老伴。但他满怀着对妻子的愧疚之情,选择了后者。1984年,老伴去世了,贺老没有被这不幸所击倒,而是更加振奋,更加坚强,料理完丧事后,他索性把行李搬到了学校。一只简易的煤炉,有时放在走廊上,有时放在墙角里,在这只煤炉上,贺老自己动手解决了一日三餐,也解决了全校五十多位教职员工的茶水。在学校,贺老既是校长,又是工友、炊事员,还兼着“值班门卫”。晚上,当师生们都回家后,贺老才能在办公室用书柜隔开的“卧室”中休息。 随着年龄的增大,也由于劳累过度,贺老患上了老年性白内障、眼底动脉硬化、关节炎等症。病痛的折磨、失明的危险,都没能使他消沉,他更加努力地工作。一边抓教学,一边治疗,使学校的教学质量不断提到提高。
1989年8月,贺老利用暑假的空隙,去加拿大与胞弟的相会,阔别四十多年的兄弟相聚,该有多少手足情谊要叙,有多少知心的话要说啊!可这一切都没拴住贺老牵挂学校的一颗心,他谢绝了亲友的再三挽留,提前回到了学校。有人不解地问他:“别人想出国还没门呢,你为何提前回来?”贺老动情地说:“原因很简单,外国再好,毕竟不是我的家,我的事业,我的家在祖国。”
萍乡中山学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仅到1991年7月止,学校共开设成人高中、职业中专等161个班,累计毕业或结业7803人。因办学成绩突出,1990年,贺老光荣出席了民革中央在杭州召开的全国办学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萍乡中山学校被评为“民革全国办学先进集体”,贺老被评为“全国办学工作先进个人”,省人民政府也授予他“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伴随着中山学校的成功,萍乡民革也逐步走进了社会,走入了人心。
五、满目青山夕照明
贺老讲,他离不开民革,自1985年第一届市委会成立以来,贺老一直担任顾问,住在机关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里,他的三个儿子各有一栋楼房,可他眷恋的还是这间小房,因为他割舍不下对民革的这份感情。直至2000年,考虑他年事已高,在民革同志的劝说下,他才回到乡下,与儿孙同住。
贺老是个闲不住的人, 几十年来,贺老曾担任省政协第六、七届委员,市政协第二至九届委员,还担任了两届市人大代表,可能是这个原因,养成了他爱管“闲事”的习惯。在村里,贺老深受大家尊敬,享有很高的威望,门口的一棵大樟树下,是他的又一个讲台,在这里,他为群众讲解时事、国家政策、法律知识,讲他出席的“黄埔同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横穿村里的那条土路,多年失修,天晴一阵灰,下雨两脚泥。见此情形,贺老又来管“闲事”了。在他的大力倡导下,镇、村、组干部召集群众在大樟树下开了个会,贺老首先发言,提出修路方案,动员大家捐款,在这次会上,就收到捐款近万元。此外,贺老还提笔给海外的亲友写信,希望他们为家乡的建设作一点贡献,仅经贺老的手,就收到海外捐款12400元。2002年3月,一条700米长,3米多宽的水泥路修成了,当地村民都称赞贺老为家乡做了一件大好事。听到这些,贺老只是笑笑说:“老父岂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
采访结束时,我曾问起贺老的那只黑提包和那张从南昌带回来的誓词,他说,那只提包还在,跟了自己这么多年,舍不得丢了,那张纸早就不见了,但是,誓言永远记在心里。
是啊,誓言在心,他忘不了自己的誓言,放不下民革的事业,几十年来,他为自己的誓言而自豪,他为自己的誓言而奋斗,几十年来,他履行着自己的誓言,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以一个长者的风范、一个民革先辈的风范,感染了萍乡民革全体党员,鼓励着萍乡民革全体同志。看着眼前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我突然不知该说什么,只是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也是萍乡民革在为他祝福,祝他健康长寿!